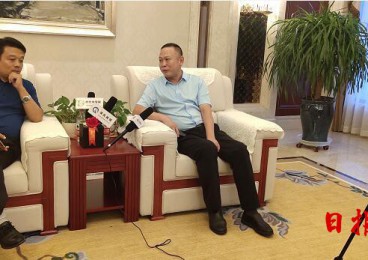10月26日傍晚,忽然收到老同事红孩的微信:“高明兄下午6点多走了。”我心中立刻漫上一片悲凉。红孩说的“高明兄”,指的是我们共同的同事马高明。

正在惊疑之际,接着又收到了微信中的讣告《永不告别》:“马高明者,山东籍北京人士也,生于1958年。自幼喜爱舞文弄墨,青年时精通英文,后成为报刊编辑,但其身份一直是诗人。然愈受缪斯之神青睐,便愈遭命运之神嫉妒,2022年10月26日18时零6分,距高明兄64周岁生日还有两周,刚刚步入壮年的高明兄,就被缪斯女神匆匆收归仙班,免却了其在人世间的所有喜怒哀乐……”翻看他的朋友圈,也看到了他夫人发出的悲哀的文字:“我的至爱、我的先生马高明……去了再也没有病痛的诗酒天堂。”高明兄一生与诗相伴,与酒相伴,可惜情路坎坷。庆幸的是他在一场大病之时能有爱情相依相伴,他们温暖又甜蜜的故事在同事们口中传颂,大家为他祝福又为他欣慰。我相信,他去的天堂里不仅有诗、有酒,而且更有美丽、珍贵的爱情记忆。
马高明兄豪侠仗义,善良透明,身边总是粉丝众多。作为初代的朦胧诗人或曰先锋诗人,他身上却没有某些所谓诗人的狂悖傲慢,总是像阳光一样让人感受到温暖和灿烂。报社的同事们说到他,思绪很快就回到当年在柏林寺办公时候的情境。
从方丈院右手的副刊部折进里间,就是马高明的办公室,印象最深的首先就是他桌上一排巍峨的听装啤酒的队列,阵容宏伟,场面壮观。在单位,他常常喜欢弄一大帮人吃吃喝喝,总是他买单,为人特大方。有时候酒菜摆到桌上,还要幽默一道,用做版的“术语”问大家一声:“今天的版式还满意吧?”话音一落,往往就引爆一阵欢笑。
当年报社领导严令禁酒,却特允诗人马高明可以享受喝酒的特权。同事们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好像都是一副手擎啤酒、仰头畅饮的形象。有时候聊着聊着天儿,他的手里就会突然冒出一听啤酒,真不知道他身上什么地方能够藏下这么多“酒泉”。
我在诗坛行走,每逢报出单位的名字,总会有人搭茬儿:“我认识你们报社的马高明。”他的好口碑,让我觉得跟他做同事很有面子,很自豪也很骄傲,往往胸脯挺得老高。马高明送过我他翻译的《希腊诗选》和《荷兰现代诗选》,都很经典。他自己留下的新诗佳作也很多,很有名气。比如《小夜曲》:“孩子们睡熟了/纷纷爬上/自己梦中的树//没有谁/打开过窗户//灯火/用渐渐微弱的语气/交谈……”这首诗凝练精致,洋溢着纯净超脱的特别魅力。诗中透过灯火“渐渐微弱的语气”,暗示出睡梦的沉静安详,抒写了心中的淡定和真醇。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高明除了写先锋诗,还经常写旧体诗。这位学贯中西的诗人翻译家,对传统文化也有着一份热忱的体味。请看这首《辛丑仲春临窗外眺》:“窗外春光滞,误我老来痴;出会蒙尘友,坐撰即景诗;无暇观叶卉,有兴品蔬食;情知眼中绿,发自陈年枝。”他的诗不拘平仄,但是颇耐咀嚼。散淡随意的窗外一瞥,见到一片新绿,引发一片哲思。当时诗人已经身患重病,但是通过陈年枝上的新绿,抒写出乐观纯粹的诗人心境。记得他因喉部手术,暂时失声之后,曾寄给过我一首《病中抒怀》:“罹癌不弃手中杯,三五相呼灯火围;披雪光阴敢问客,思人滋味怯看梅;韶华红绿年年有,淡漠阴晴日日非!不知今朝风月梦,能否来岁报春归?”诗中真实地表达了他对病痛的无奈和忧虑,同时更抒发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执着。我也曾寄他一首《赠马高明》:“檀溪风雨连天起,一跃沧波信可期。暂教春雷心底歇,于无声处待新诗。”

高明做手术之前,曾经把自己的《春天》《影子之歌》《仲夏行为》等代表诗作朗诵录音,做成光盘,留存下了珍贵的声音。他给世界留下的记忆,永远是那个潇洒奔放的激情诗人。他大气达观,很够朋友,同时他对人对事又爱憎特别分明。记得有一回我去他和平里的家中看他,他刚开始练习用声带发声,说话十分吃力,看得人想哭。但是他隔着口罩欣喜地说,已经又能喝啤酒了,干脆连吃药都用啤酒冲服。当时病成这个样子,他还不忘照顾客人的感受,邀我看他新写的诗,看他收藏的画,还愤怒地和我回忆某某诗人薄情地伤害一位女孩的事情。可惜我不善饮酒,无法陪老兄畅饮,只好陪他一起冲着窗外的空气,痛骂了那位薄情郎一番。
高明兄得风气之先,曾经张罗着下了一段时间的“海”。他先是在团结湖公园西门办九月画廊,后来又牵头办了一个公司,搞文化项目的策划,研究地方文化概览,进行文化设施巡礼。可惜激情和浪漫并非商海的通行证。他的买卖好像终究没有多大起色。最后沉浮红尘,累了一身重病。但是无论道路怎样曲折,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马高明永远是挺直脊梁,硬架不倒,真是令人佩服。我曾去参观过他在南戴河买下的海景房。那间一居室的客房阳台直接面朝大海,可以高眺云水苍茫的辽阔远方。那扑面而来的海浪翻滚奔腾,倒也恰似姓马的诗人那不肯停歇的灵魂在日夜奔涌、奔腾,外表充满活力而内里也暗含着许多看不见的苦涩。他在《春晓》中写道:“晓来无意怨早春,大梦三冬好听琴;不恋初晴千般好,但爱晚霞一片心;连年染恙难破壁,终日啼血易断魂;半世浮尘应无悔,白条浪里共佳人……”从诗的最后两句,可以想见他在历经沉浮之后的生命感悟和对爱情的珍惜。
早就知道高明兄身患重病,但还是觉得噩耗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两个月前参加作协的诗歌评奖活动,遇到过和马高明一起翻译《希腊诗选》的诗人树才。树才问起高明的身体状况,我还说患病10多年了,已经稳定下来了。前些天和同事昱老师谈起高明兄,她也说总觉得高明兄的身体能够撑下来了,将来要找机会去看望他。可惜生命毕竟是脆弱的。病魔不肯停下来等人,而人等来的“将来”,却是永远的离别。昱老师深情回忆,当年刚来报社时,有一次版上某篇文章受到领导批评,心里正郁闷,恰好窗外树上传来喜鹊欢鸣,高明就细心地过来安慰说:“以后喜鹊来了也不能信了。”一句打趣的话,就把人逗笑了。喜鹊的喳喳不能信,高明的话却很灵验。他用他特有的真挚、温暖和风趣,很容易就驱散了小同事心底的阴霾。

我们工作的副刊部门,编辑队伍中先后有马高明、林白、红孩也包括我,不少诗人在此相继供职。无论相聚的时间长短,有幸留下一份真挚的诗缘,多少年之后仍然能够回忆起彼此的一些趣事或糗事,一脉诗缘,连绵不断,延续至今。每位诗人个性不同,但是率真的性情则是相同的。尽管命运时时做着加减法,而记忆则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庆幸工作和生活中总有一份诗意,让人心变得柔软和温暖。试想,倘若一个单位都是“插刀教”,互相之间充满冷酷算计,这样的相处环境将是多么令人疲惫啊。
高明远行了,诗还在,情还在,那长满大胡子的向日葵一般的笑脸,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