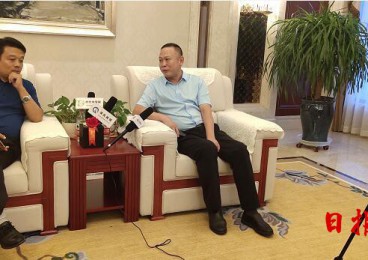在书法学有望升级为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中一级学科的背景下,积极拓展学科层次、挖掘学科深度、充实学科内涵,是当前开展教学教研的首要任务。作为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篆刻学理应得到学理研究上的重视和支持。如何将篆刻学学科建设推向更加系统化、学科化的高度,从而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品质?
▲ “书学之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成果系列之篆刻专题展”陈宇作品
印学研究涉及丰厚的跨学科学术内涵
近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线下、线上同时进行的第四届“书学之路”论坛就结合篆刻的发展现状,首次提出了“从篆刻到印学”的研讨主题。与会学者结合自身研究课题,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对吴昌硕、陆维钊、方介堪等篆刻家、印学家刀法与笔法的深入探索;有对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印学文献的鉴藏与考证,并深入挖掘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印学观念及其存在方式;也有从篆刻与印学的范畴差别、印学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印学主体与本体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的分析和思考。
“从篆刻到印学,是将历史的责任与当下的形势衔接起来。”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表示,印学研究涉及文字、文献、历史、考古、制度、职官以及艺术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具有丰厚的跨学科学术内涵。
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许江也表示,篆刻艺术不仅是刻字,更是用排布呈现独特的意象,简约而渊博,具有直落山河的大气之美。篆刻的核心在于金石学与古文字学,其又涉及儒家朴学的经典,彰显着中国学术的高端地位,因此,篆刻学本身亦有山河之壮。因此,此次论坛将篆刻提升为印学,从艺升华为学,尺度提高、视野开阔,凸显了篆刻艺术及汉字研究在近年来的显学之势。以陆维钊、诸乐三等大师为例,许江启发后学者不仅要做好国学梳理,进行金石学、古文字学等知识储备,还要加强方法论的研究,把篆刻技法的基本问题研究好,将篆刻与印学的核心与学术不断丰富。
▲ “书学之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成果系列之篆刻专题展”罗俊杰作品
“印外求印”与培育“通人之学”
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离不开陆维钊的贡献。1960年,应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之邀,陆维钊由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与沙孟海一起,开创了我国现代书法教育的学院体系。其后历经十年浩劫,1978年返校,1979年以80岁高龄招收研究生,其间,陆维钊为首届研究生制定《教学纲要》,其中包括关于书法篆刻的60个问题。在陆维钊看来,自古以来,能够书、画、印、诗兼通而均臻精绝者非常之少。其中,尤以印为最难,因为它最小而变化万端;此外,其学养最深奥。欲求篆刻艺术之高超,工夫反在印外,这和古人论诗之“工夫在诗外”是完全吻合的。这种观点归纳起来就是“印外求印”。他对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学生的教学思想中,就有书法必须深研文史、篆刻必须精于古文字(金石)学这条。
虽然已经过去40余年,但陆维钊设定的教学框架依然对当前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认为,陆维钊提出的著名的60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美院书法专业“诗、书、画、印”兼通以及外延入各个学科的蓝图,外延之途径为文化史、考古学、文学、史学和哲学。“尤为关键的是:陆维钊将甲骨文列入学习对象,并引用董作宾殷代书法‘五期说’,又将金文的作品分别归五类加以学习,如散氏盘、兮甲盘为浑穆苍劲类,大盂鼎、师遽簋为雍容闲雅类,王孙钟、邾公坙钟为顾盼婀娜类,齐陈曼簠为轻灵细锐一路,宗妇鼎、秦公簋为疏散磊落之属。此种分类法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颇有相似之处,但较之康氏则更有其可教可学之道。尤其是他以上古文字直通隶、篆书道,对高等书法教育至为关键。由于陆先生的远见卓识,中国美院之书法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即开创出一种培养‘通人’的模式,通达于古文字、金石文献、经史之学,旁及文学辞章之道。”高世名说。
▲ “书学之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成果系列之篆刻专题展”胡志龙作品
“印之内”与“印之外”需要把握好度
近年来,随着印学研究的范围、深度和规模有了显见的进展,“大印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就提出,应当把碑帖的传拓技术、域外印章、印谱史等研究,都纳入“大印学”概念。
“‘大印学’是对传统印学坚守与超越,它的根基一定也只能是传统印学,这点毋庸置疑。但它又不限于中国传统印学以《说文解字》、‘六书’理论、篆书为应用基准的这样一种印章观。‘大印学’的新格局中,我们对于印章的应用方面(文字运用和印材运用)会有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拓展的意思,就是说‘大印学’中的印学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文献和学术,还包括我们的材料和技能。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开放又理性的观念和思想。”基于此,陈振濂还提出了“大印学”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一是推进“砚铭文化”,二是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三是倡导“拓片题跋”,四是“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
“大印学”对于篆刻学学科建设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莫小不认为:“从学术意义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立足于本体,即篆刻本身,但是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延伸。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原先篆刻主体上拼命去挖掘,有时篆刻甚至和印刷、跟商业等都会联系起来。从高校的学科建设来说,从理论研究、项目申报来说,领域的拓展、延伸、交叉,产生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东西,这些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的‘大印学’概念,恰恰是把边缘做得更大了。如果我们填补了一个从来没人想到过的领域的空白,会觉得很高兴;但也可能在某一领域与其他学科连接、重合,恰好跟原来不是同行的一个人相遇、相知、牵手并合作,做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果,这可能更有价值。从学科的性质角度来说,‘大印学’概念的提出,让我们用关联思维去涉足新的领域、创造新的成果。”
显然,在学科细化的今天,“大印学”的提出可以避免印学研究往更加细枝末节的方面越走越窄,而是以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关注印学的外延,包括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大印学”还可以解决印学以外被人忽视的交叉学科甚至是其他学科的问题,比如说玺印文字、古文字学的研究,印学也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两方面又有不同侧重。古代职官、历史地理,本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任务,但印章里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印学的参与具有专业优势和专业方法,比如鉴别、断代,文字的释读等等。如此,“大印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但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金丹也提出:“无论是印学还是‘大印学’,都应该重视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大印学’,如果完全突破了边界,就会成为一个大杂烩,突破了这个边界,可能不但不能称之为‘大印学’,反而会变成什么学都不是。因此要把握一个度。当下可能需要靠研究者去主观把握,但将来应该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概念和标准去规定它,让它有一个清晰的边界。”
西泠印社兼任印学理论与社史研究室主任孙慰祖表示:“我们研究基点在‘印’和‘从印出发’,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是相关性的延伸。印学今天强调的‘大’,我的理解是印学仍然是一个小宗,但它的学术框架可以放大。微观的研究需要宏观的学术视野。就学科定位而言,在‘印之内’与‘印之外’这两个方面,应该有非常好的把握。印学的学术地位与当代价值,在于它在整个时代的精神生产中占有多少真实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