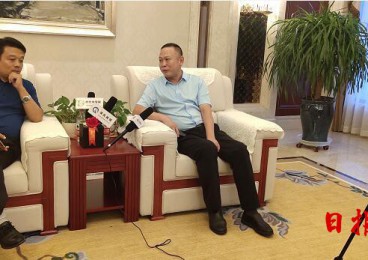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
湖北宜昌与吉林四平相距2000多公里,如果不是因为一篇报道,68岁的王胜利与80岁的王永红今生怎么也不会相识,更没有这段“以报为媒,以文结友”的佳话和今天王胜利评王永红长篇小说《父爱》的君子之交。
2021年12月31日,《中国文化报》8版头条配图刊发胡振栋、胡芳采写的人物通讯《王永红:土家山寨“最美文化人”》。吉林省四平市散文作家、评论家王胜利读后,深为王永红的先进事迹所感动,也为其一辈子钟情文化、勤奋笔耕的创作成果惊叹不已。
今年2月初,王胜利给王永红写信表达敬仰之情,希望得到其题赠的长篇小说《父爱》等作品用于学习收藏。王永红虽然家中早已没有《父爱》等存书,但为了不让远方的文友失望,又到别处收齐题字后邮寄给王胜利。
读罢《父爱》,王胜利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乘兴写下《秋光依旧似春光》书评,并通过邮局寄给王永红。现将此文予以编发,以飨读者。
最近,我收到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退休干部、乡土作家王永红先生题赠的四部大作——《父爱》(长篇小说)、《抱朴斋文选》(小说卷·上)、《抱朴斋文选》(小说卷·下)、《抱朴斋文选》(诗歌卷)。这次集中阅读王永红先生的小说、诗歌集里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通过阅读,我不仅得到了美好的艺术享受,还唤醒了不少沉睡的记忆,激发起不少写作的念头。我每天沉浸在王永红先生的小说、诗歌里,读得有些忘我,并从中获得了精神力量。
《父爱》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长篇小说。在鄂西与湖南交界的清溪湾,这是一片充满历史烟云的厚土。《父爱》以30多万字的篇幅,描写二十世纪40年代直至今天(七八十年间)发生在那里的乡土生活,揭示了人们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在社会急骤变革和巨大转型时期的残酷命运,以及普通人(父亲)在苦难中面对迭连而来的厄运辗转求生,坚韧地承受一切打击而迎来转机的经历,昭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而永续存在且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因。
本书主人公父亲(曾明俊)为养育和庇护、教育子女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体现了博大的父爱,甚至可以说,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典型的鄂西父亲的崇高品质。但无疑,父爱一词并不能概括父亲的一生,他还有贯穿其一生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种爱,生而可以死,死又可以生,惊天动地、充满畸变而带有悲剧色彩,也正是这样一种爱情,决定了他的人生是由一道道惊涛骇浪组成的大河;又是在这些浪涛的激荡下,方显出其人性的光辉。
《父爱》小说中还描绘了众多呼之欲出的乡村人物形象。那些人物形象当中有作者(我)的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伯父、姑姑、叔叔、舅爷、妹妹、弟弟等至亲,还有村里的大娘、嫂子、堂哥、堂嫂和儿时的小伙伴等。除了第一主人公父亲(曾明俊),小说中这些主要人物的塑造也是立得住的。作者在写他们的时候都不是从概念化出发,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生活实际出发,用符合生活逻辑的故事情节去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
作者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所记所感,忠实得甚至有些平实,让人想到散文,想到传记。正是这样的写法,使我读来感到亲切、贴心、饶有兴味。作者的写作态度是诚挚的,他觉得有感情要抒发,有心里话想跟亲人、朋友们说,就真诚地、全身心地写起了这部小说。写小说,对年轻的作者来说算不得什么,但不要忘了,王永红先生当年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写作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值得称道的是,他写的这部小说一点都不摆谱,一点儿都不假装,通过小说袒露的是一个作家厚道的天性。
在《父爱》小说中,“爱与善”是贯穿父亲(曾明俊)一生的内涵与品格,是穿越人世沧桑、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够生发出来的光辉。他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能释放最大的善意,给予他人关照和温暖。可以说,他所到之处,他所播下的都是亲和与善良的种子。而且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应当、必须去做的,这种无私、这种利他精神出自一个边远乡村男子汉的天性,是多么感人。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把他夸大,没有特意把他写成一位伟大的父亲,作者一直在写他的苦难,写出了他的艰难竭蹶,写出了他的束手无策,写出了他即使在生活的磨盘底下喘不过气来,也始终隐忍坚强,竭力把事情向好的地方转化,就像一只公鸡,在风雨中张开翅膀庇护他的孩子与亲人,从而显示一位父亲伟大的一面。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整个鄂西男人的影子,他是鄂西男人的杰出代表。作者写出了鄂西人尤其是鄂西男人的内在秉性与外在特点,小说塑造的父亲始终把别人的利益与感受放在第一位,可谓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由此我们可以推想,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把根深深扎在如此深厚的美德土壤里,才能经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不被摧折。这正是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推荐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父爱》这部写满疼痛但更多的是写有温暖的小说中,作者不为父亲讳,不装饰美化父亲,也用一定的笔墨再现生活中父亲直性子和暴脾气的另一种存在。作者的实诚写作,达成了对父亲独特人生、人性和人情沉郁透亮的呈现。正是这样的写作,使父亲的精神形象得到了立体而独特的建构。父亲有着父亲的顶天立地,也有着他的匪夷所思和种种缺失。只是一切都是这样的真实、真切和真诚。从某种意义上说,《父爱》是一部实录父亲人生与生命的书,是一部儿子走近父亲灵魂的倾诉和理解之书。
《父爱》以时间为经,世事为纬,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但在叙事上又能够从容叙事,紧针密线,布局谨严,可谓严丝合缝,这有赖于作者对故乡鄂西、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以及风土人情的谙熟,所以写来似乎举重若轻,有条不紊(其实乃是经过几易其稿)。可以相信,这部书中的许多人物原型都是他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所以他写来不仅逼真,亦饱含感情。这种感情也是对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的深情。这是这部作品之所以能立得起来,并相信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内在灵魂。
判断好小说的标准有多种,除了看小说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共情、共振、共鸣,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小说是不是一篇激发之物。好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止于欣赏,不是读完就完了,它还是一种诱发之物,或者说是激发之物。它是激发记忆的记忆,激发想象的想象,激发语言的语言,读王永红先生的小说《父爱》就是这样,捧读之间,对我的记忆有所激发,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我父亲于1994年去世,我母亲于1996年去世,我永远怀念他(她)们。我相信,只要与自己的父母亲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读者,都会从书中找到共鸣之处。
囿于篇幅,王永红先生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诗歌作品,兹不再述,有待以后品鉴评论。
我与王永红先生结识,缘于《中国文化报》一篇报道。2021年12月31日,《中国文化报》8版头条刊发胡振栋、胡芳采写的4000多字人物通讯《王永红:土家山寨“最美文化人”》,我一口气读完,深为王永红先生的事迹所感动,也为其一辈子钟情文化、勤奋笔耕的创作成果所惊叹。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今年2月初,我斗胆冒昧给王永红先生写了一封索书信。信发出后,想想真有些贸然,我与先生非亲非故,仅凭一纸信笺,先生能赐赠我作家题赠本吗?大约半月后,先生发来短信,他表示分文不取诚意相送(因他手头无存书了,他会去县图书馆想办法收集为我赐书)。一般来说,作家对于自己的著作,多是自珍自重钟爱有加,甚至达到秘不示人的程度,像王永红先生这样慷慨赠书实属少见。令人不能忘怀,先生对我可谓至诚至情至性矣。
面对先生义重情深的赠书之举,我感到如此珍贵的礼物出手得越是平常、或是随意,反过来,越显其传奇,传递的人间情谊有如水一样清澈透明,有如歌一样美妙动人。
如果说在王永红先生长期耕耘的群众文化和文学领域中,能清晰看到他为文的品格,那些看似微小的人生细节,则更能看到他为人的性情。我觉得这已经蔓延到文学之外,文品与人品互为镜像。
我还是从书中字里行间看到,先生对生活仍一如既往地深情,对亲友仍一如既往地深情,对年轻作家仍一如既往地深情,这是三幅活色生香的温暖画面。这三幅画面是品性,是情感,是心地,超越了文化、文学的范畴,可以影响读者,也影响自己。
合上书卷,意犹未尽,写下一首打油诗,作为读后感。并祝福王永红先生八十大寿。
痴迷文学一生忙,八十风霜染夕阳。
朴斋文选留岁月,清新淡雅好文章。
情系桑梓掖后辈,幽谷开花晚后香。
青山踏遍不辞老,秋光依旧似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