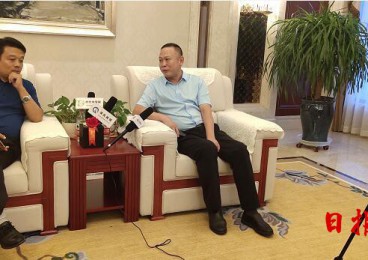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确定了文艺工作的指针。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聆听有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故事,学习党领导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勇攀艺术高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贺敬之 作者供图
贺敬之是著名的社会主义文艺家,他少年时即好学上进,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烧到家门口,不得不离开家乡山东峄县(今山东省枣庄市),流亡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尽人间冷暖,尝遍生活苦辛。直到1940年奔赴陕西延安,他才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也迎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 贺敬之作品 作者供图
在延安,贺敬之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接受了系统教育,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精神指引下,扩展自己的艺术视野、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1945年,刚20岁的他就参与创作了革命文艺经典《白毛女》,在《太阳出来了》的旋律中迎来中国的新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倾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作了《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鼓舞人民心劲的政治抒情诗。改革开放后,他担任文艺战线领导工作,同时创作了诸多新古体诗,深受读者喜爱。
小学时,我就背诵过他感人至深的《回延安》;中学时,又诵读过他催人奋进的《雷锋之歌》;上了大学,更是大量阅读他的诗作。等2001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后,随着学习系统化,我对他作品的认识更加深入,从中体会到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一路走来的艰难,也从中体察到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高远追求与光明前景。读着作品,有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能见他,听他谈谈,该有多好啊!
强烈的向往成为现实!2004年,在导师韩毓海的指导下,我和几位师兄弟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了几篇讨论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论文,或许是文章观点比较鲜明,文字也有朝气,我们这几个无名小辈的文章竟引起了这位大文艺家的注意,他委托编辑部联系韩毓海老师,请他带我们几个去他家座谈。就这样,我认识了可敬的贺老,而且以后每年我都去他家看望几次。2016年我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工作,出于工作关系,我跟他见面的次数更多了,当面聆听他教诲也更经常了。
跟贺老见面,除了日常问候,谈的最多的就是文艺问题——他非常关心当代文艺发展状况,也非常关心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状况。每当谈起这些问题时,他不仅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而且总是语带真情。
记得2004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谈到了《白毛女》,也谈到了当时普遍关注的“三农”问题。当谈到有些地方农民生活还很苦时,他几次长久地沉默和叹息,眼中也泛起了泪花。其凝重肃穆的神态让人敬重,也让人亲近。
贺老对人民的真情既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既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情感表达,也是一位革命文艺家责任心的自然显现;既具有深厚的情感基础,也具有深刻的理论因由。说到底,这是因为贺老有着喝着延河水、吃着延安小米饭长大的深情;是因为贺老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的磨砺与淬炼,炼成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真心;是因为贺老捧读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之“书”的浸润。正因为如此,当他重回延安,才写出了“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的动人心曲,才念念不忘“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作为一位革命文艺家,贺老“手中的书”自然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用2002年纪念《讲话》发表60周年他接受河北电视台记者访问时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我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我去看望贺老时,时常听他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有关情况,谈到《讲话》,谈到《讲话》的影响。贺老并没有现场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但他却是《讲话》精神的受益者、践行者、倡扬者,因为座谈会后,毛泽东同志专门到鲁艺给老师和学生们讲过一次课,给他们“吃过小灶”。
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会议举行后,鲁艺一些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很不甘心,一方面找参会者了解会议精神,另一方面去找周扬,要他请毛泽东同志来给大家讲一次。周扬去请,毛泽东同志答应了。据贺老回忆,是他首先发现毛泽东同志来鲁艺的。那天他本来有事要出去,走到学校门口,看到毛泽东同志就要到了。他非常高兴,就大喊着回校内报信去了,并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找了个听讲的位置。毛泽东同志主要讲了“小鲁艺”和“大鲁艺”的关系问题,说“小鲁艺”的学习当然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忘了“大鲁艺”,不要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要向社会学习,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贺老回忆说,他不仅那次听得非常认真,而且想方设法了解有关座谈会的情况,如饥似渴地学习《讲话》。
贺老不仅从理论上学习、接受《讲话》,而且按照《讲话》指出的方向,积极投身到革命文艺实践之中。座谈会之后,在周扬领导下,鲁艺发起了“新秧歌运动”,成立了鲁艺秧歌队。贺敬之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秧歌队的活动,从1943年到1944年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并在一些小型、中型的秧歌剧创作中担任文字执笔,创作了《栽树》《瞎子算命》《周子山》等秧歌剧,还创作了《七枝花》《南泥湾》等歌词。贺老参加秧歌队的活动,不仅要在“小鲁艺”学习,而且还要经常下乡、下厂,进入“大鲁艺”,向社会生活学习,向人民大众学习。正因为如此,今天读到他当时创作的这些作品,不仅能够感受到其中涌动的诗情,更能够感受到洋溢其中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可以说,这是贺敬之实践《讲话》精神的初步收获。更重要的是,正是这样的综合锻炼,极大地提升了贺敬之的艺术才能,使他之后能执笔参与创作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歌剧《白毛女》。
《讲话》发表至今80周年,贺敬之由革命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小兵成长为一位老兵、强将,在不同时期均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成为实践《讲话》精神的优秀代表。
我第一次去见贺老时,他已近80岁高龄,可多年来,每次去看望他,一谈起延安,谈起延安文艺,谈起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来,他总是兴致勃勃、精神愉悦,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这让我不时想起他初到延安时写的《生活》这首诗,想起其中“我们是小麦/我们是太阳的孩子”这句诗来,心中有无尽的暖意。
我理解,“太阳”就是共产主义,就是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先进思想理论,其中自然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接受“太阳”的照耀时,卓越的文艺家自己也供给“太阳”以热源,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壮大着“太阳”的光辉,丰富着“太阳”的色彩。
我们敬重这“太阳的孩子”,我们学习这“太阳的孩子”。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