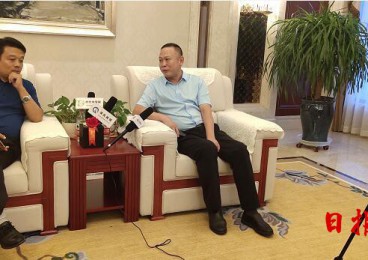鲁迅先生不仅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同样也是一位出色的美术鉴赏家与活动家,然而他编辑笺谱的经历,对许多人来说也许还很陌生。由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共同编辑、复刻的《北平笺谱》与《十竹斋笺谱》,不仅造就了中国木刻断代史上的丰碑,更留住了传统彩色套印版画技术的火种。他编辑《北平笺谱》与《十竹斋笺谱》过程的始终,正离不开一个“情”字的推动。
鲁迅提出编辑一部笺谱的成熟想法,是在1933年初。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上加序目,订成一书,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
鲁迅编辑笺谱的想法并非心血来潮,冥冥中的第一推动力正是他去世多年的故友陈师曾。早在1928年筹备散文集《朝花夕拾》时,他就希望用陈师曾的花卉笺纸作为封面,可惜委托的学生未能找到,只好作罢。陈师曾在江南陆师学堂和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与鲁迅同窗相处,两人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并亲自设计封面,封面的题字正是陈师曾手写的铁线篆字,书法古雅静穆。两人民国初期同在教育部任职,一起为博览会选定展品,一起逛琉璃厂淘宝,一起出门寻访师友,为鲁迅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亮色。然而天不假年,1923年陈师曾为母亲探病时意外染病去世,年仅47岁。
鲁迅编选的《北平笺谱》共收录笺画332幅,其中陈师曾一人独占32幅,一人即近总数的1/10,包括山水、花卉、刻铜、书法等广泛题材。历经10年的寻找与编辑,鲁迅终于用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陈师曾不朽的怀念。
鲁迅先生在编辑笺谱过程,对待那些他从未有过交集的画师与工匠,也都满怀着善意与真情。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嘱咐道:“(画师)李毓如在光绪年中,似为纸店服役了一世,而技艺却实不高明,记得作品却不少。”“吃苦而能入书,虽可笑,但此书有历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鲁迅没有食言,《北平笺谱》精选了李毓如绘制的梅兰竹菊四君子笺。此外,《北平笺谱》还收录了琉璃厂画师戴伯和、李伯霖、刘锡玲等人的笺纸。鲁迅执意将平凡的画师录入艺术史,为后人保留了更多的参考样本和一个个值得铭记的名字。
刻工虽然在雕刻笺版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却因为是体力劳动者,被人呼来喝去,“刀头具眼”的神技也被视为“贱技”。鲁迅暗暗为他们打抱不平,他采取的编辑举措,一是在《北平笺谱》目录中将刻工的姓名与画家一同列明,二是请郑振铎在后记中专门记录每个人的姓名与所属的笺肆。后来,他和郑振铎每月共同出资约50元钱,作为补贴绘刻《十竹斋笺谱》的费用。中国1930年代的物价稳定且低廉,在北京三间厢房的月租金不过6元钱,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每月伙食费15元,50元可以买800多斤大米,这笔筹款是相当充裕的。
鲁迅收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后,一边由衷肯定笺谱复刻的高水准,一边对刻工进展速度之慢也颇为无奈,“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鲁迅似乎和工匠之间有一种“消极的默契”,他一方面盼望着笺谱尽快完工,另一方面又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去资助工匠,延续工艺。在去世前20天,重病中的鲁迅仍心心念念《十竹斋笺谱》的进度,他去了最后一通短信问郑振铎:“《十竹斋笺谱》近况如何?此书如能早日刻成,乃幸。”其中的语气已经十分虚弱,更像是祈祷一般,有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无可奈何,这在鲁迅的行文中是极为少见的。虽然当今世人看到鲁迅先生的,多是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但他对素未谋面的画师与工匠,竟抱有深厚的同情与宽容,可谓“俯首甘为孺子牛”。
如果以鲁迅为圆心,以笺谱事由为半径画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便可以充分感受到他的处世之道与交友之情。作为《北平笺谱》与《十竹斋笺谱》的共同编者,郑振铎无疑是鲁迅先生格外倚重的人。他在与郑振铎的通信中,并没有客套与赘言,令人充分感受到信任带来的温暖。鲁迅先生在经济上也是无条件信任郑振铎,几次主动预支大额费用,不让对方有一点为难。就连郑振铎垫款买的笺样,鲁迅也替他牵线,转售给了内山书店。
鲁迅先生对待亲近的朋友如此,对陌生的读者也视作“上帝”而一视同仁。当他查到过手的《北平笺谱》装订时偶有缺页,遂逐一向郑振铎指出漏掉的笺纸页数,并语重心长地请后者及早加印寄回。当他看到《十竹斋笺谱》的古雅与精美,不止一回想到的却是囊中羞涩的美术生,并另想办法印制平装普及本,将这份古典艺术珍品普及给有需要的学生。
许多大人物不屑一顾的琐事,在鲁迅先生眼中却都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这种温暖全然出于本心,不仅让身边人倍感亲切,更让后人感到他人格的伟大。
《北平笺谱》一函6册,初印100部,鲁迅先生自存及送人20部,首版很快售空后又加印了一百部。能获赠这样一部珍贵大书的人,在鲁迅心中各有珍贵的情谊与因由。
《北平笺谱》是一如旧制的线装书,手书题签必不可少,鲁迅心中的人选是老相识的“新青年”。封面题签沈兼士、扉页题签沈尹默都是鲁迅当年在北大的同事,序言书写者魏建功是他在北大的学生。对于书法家,这或许只是举手之劳,但鲁迅满怀着欣慰与感激,向三人分别赠送了笺谱。
鲁迅先生对于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则是格外的坦诚与周到,生怕对方有为难的情绪,处处照顾对方的自尊。他将这样一部珍贵的大书赠予看重的青年,首先声明的就是不收钱。无论是“未名社”的台静农、青年木刻家陈铁耕、青年编辑杨霁云,他都每人免费赠送一部笺谱。
在鲁迅寄赠《北平笺谱》的人士中,还有几位外国的友人。增田涉对鲁迅先生执弟子之礼,曾向他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之后将《中国小说史略》翻译成日文。山本初枝女士——也就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提到,将“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写给的日本歌人,她寓居上海时结识了鲁迅先生,常给鲁迅儿子周海婴赠送糖果、衣服、玩具等小礼物。这两位友人回到日本后,鲁迅与他们依然保持着通信与友情。他曾向山本初枝预告笺谱将要出版的消息,“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在印《北平笺谱》,预定明年一月出版。出后当寄奉览。”鲁迅先生还特意托内山完造的朋友将《北平笺谱》带到日本寄给增田涉。增田涉去世后,将所藏图书捐赠给任教的日本关西大学,其中就包括这部初版的《北平笺谱》,笺谱的扉页留有鲁迅先生的手书赠言,使得这份跨海的深情仍历历在目。
后人展开这样一部《北平笺谱》,犹如瞻仰一座高山仰止的传统美术丰碑,丰碑上写满了鲁迅先生对逝者的怀念之情,对朋友的脉脉温情,对辛劳者的真切同情。正应了他留下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