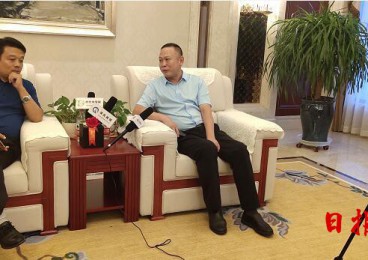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孙亚玲

1985年,改革开放的号角早已在神州吹响,在我的老家峒峪村,父亲一手端着筛子喂牛,一手拿着报纸,渭南同州餐厅一则招聘信息引起了他的兴趣。
当时,我们家是村里最早饲养奶牛的专业户,槽里拴着八头大奶牛,算得上是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家庭了。在此之前,我们家很穷,孩子多,四儿一女,生活的担子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20多岁大哥的婚事更让父母操碎了心。有一天热心的花娘来到我家,和母亲在厦房里小声地商量着什么,谨慎又神秘。我和弟弟还小,被母亲支使着到村前头的合作社去买盐。
几天后,花娘领着她的外甥女来到我家——看家。父母热情地招呼着,不但擀了碱面,还烙了葱花油饼让她们吃。大哥陪女孩坐在西边的旮旯里,弟弟很好奇,偷偷趴在门缝儿朝里看,大哥递给女孩一缸子热水,女孩腼腆地接过来,端在手中并未喝,弟弟急得大喊:“快喝,是白糖水!”女孩的脸一下子红得如天边的火烧云。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大嫂。
父亲卖了家里正产奶的奶牛,带着母亲、大嫂和两个哥哥,来到渭南做起了餐饮生意。“蓝田小吃”的招牌在渭南长途汽车站一间门头上挂了起来,卖的是母亲做的葱花油饼。
我家的葱花油饼,用的是真材实料:上等的面粉、纯正的压榨菜籽油、新鲜的小香葱。用木炭文火上下两面同时烙、烤、煎、烘、炸,两面焦黄,皮酥内软,面白葱绿,油汪汪的葱花油饼还没出锅,香气就弥漫在空气中。葱花油饼搅动着人们的味蕾,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小吃,很快就名噪一时。
美食是最有诱惑力的,我家的葱花油饼吸引来了渭南作家李康美先生,基本上每天早晨他都会来吃,两块葱花油饼,一碗稀饭,然后到单位上班,并从不吝啬地宣传葱花油饼的美味。
第二年暑假,母亲把我接到了渭南,每天清晨看着饭店门口排起的长龙,我也不能闲着,帮忙收钱、拾掇桌子。
一天中午,父亲带来一位姓陈的叔叔,陈叔与父亲有着共同的爱好——文学,他们就在客厅里热闹地谝闲传。母亲烙了几张葱花油饼,她端着刚烙好的中间十字形切开的葱花油饼,无数个油泡在饼子表面“扑腾腾”地闪动着,黄亮中透着微红,诱人的香气在院子里飘荡着。还没等母亲走进客厅,陈叔站起来撩开竹门帘,拿起了一块,他边吃边说:“嫽咋咧,老嫂子的手艺嫽咋咧……”陈叔狼吞虎咽一连吃了三块,两手一拍笑着说:“这么好吃的东西,回去时给你弟妹带几个,让她也尝尝。”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陈叔就是著名的作家——陈忠实。从那以后,陈叔常常来我家吃葱花油饼。
1994年,我在省作家协会文印室工作,正好和陈叔的办公室面对面,与陈叔的来往更密切了。他经常来打印室打印他写好的文章,陈叔对我就像对他自己的子女一样。有一天,陈叔对我说:“女子,回去给你妈说,明天给叔烙上几个葱花油饼,我想去你家吃饭哩!”
母亲当晚泡好酵头,早晨起来发好面,在城墙根早市买回沾着露水的小香葱,把根须和老叶摘掉,只留下葱白和嫩叶切碎,在盐里搅上她特制的以小香、花椒岀头的五香粉备用。
上午10点多钟,陈叔来了,刚一进门就冲父亲说道:“兴盛哥,我又馋老嫂子的葱花油饼了。咱俩好了几十年,我也吃了你家几十年的油饼子,就连我的《四妹子》和《蓝袍先生》都是吃着你家的葱花油饼写出来的!”父亲和陈叔站在厨房门口说笑着。母亲手上抹上菜油,从面盆里拿岀发好的面团,在案板上来来回回使劲地揉着,陈叔对母亲开玩笑地说:“老嫂子,你烙的葱花油饼好吃筋道,是不是像我兴盛哥常说的,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母亲点点头说:“不但面要揉到,还得软和,要软得刚能捞到手,更重要的是酵头发面,碱面也要放合适。”母亲说着,把揉好的面团滚成一个个圆形底子,四周刷上菜油并排摆在案板上,用盆盖着醒20分钟。然后,用小擀杖一边旋转一边擀成长方形的面片,先抹一层用大油面粉菜油搅拌成的调和油,撒上五香椒盐,把葱绿葱绿的小葱末均匀地铺上一层,再从右边开始一边拽一边卷,拽得越薄、卷得层越多,烙出来的葱油饼就越酥。面团在母亲手里像变戏法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滚成碗口般大的圆球,再用手掌压扁,拿起擀杖在案板上咚咚地敲两下后,才擀岀一指厚的圆面饼。母亲双手一提,放进鏊锅的滚油中,“吱溜”一声,菜油的香气便充溢了整个厨房。
母亲把木铲子伸进饼子底下,“嗖”地翻了个身,葱花油饼用手指划岀的“沟壑”里,油花花在热热闹闹地泛着,沟壑外被热锅烙了的部分呈现出黄中带红、红中带紫的焦糖色。母亲从鏊锅里取出外焦里嫩的葱花油饼,在案板上“咔咔”剁两刀,一块变成四块,陈叔拿起一块吃了起来,说:“老嫂子,这葱花油饼味道没变,跟在渭南时一模一样!”
父亲和陈叔有着几十年的交往和友情,陈叔去世以后,我家很长时间没有烙葱花油饼。偶尔烙葱花油饼时,父亲就会念叨起陈忠实叔叔,思念着他逝去的老朋友。
坐在电脑前,当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出“葱花油饼”几个字时,陈忠实叔叔那熟悉的面容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敦厚朴实的脸庞,沟壑交错的皱纹,黑亮亮的眼睛,两位满头白发的老友面对面坐着,吃着刚出锅的葱花油饼,聊着文学,聊着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