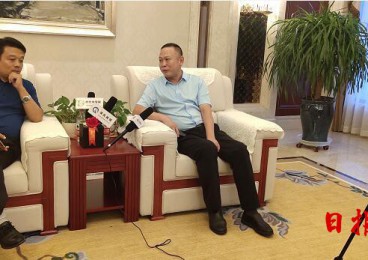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文旅中国 作者:刘茜
 ▲ 刘茜 摄
▲ 刘茜 摄
陈彦简介
陈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创作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装台》获2015“中国好书”、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主角》获2018“中国好书”、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从“西京三部曲”为代表的舞台艺术精品,到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著名作家、剧作家陈彦以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获奖无数,赢得了戏曲观众与小说读者的共鸣,又以近期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剧《装台》而走入了千家万户观众的心中。数十年来,陈彦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努力开掘普通人的生命价值光亮,从传统中获得营养,从生活中汲取灵感,以对人心世事的深刻洞察,以旺盛的创造力,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不断从创作的高原走向艺术的高峰。为此,本文以独家专访的形式,试图从一位优秀作家、剧作家个案的角度,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诠释艺术创作的真谛。
记者:您怎样评价电视剧《装台》?听说您的小说《主角》未来也将被搬上荧屏,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剧本改编阶段,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
陈彦:电视剧《装台》改编得好,导演、演员也做得很好。他们做到了尊重原著,无论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都是朝着现实主义路子改编的。作为原著作者,我向他们致敬。
电视剧有它的创作规律、市场规律,和小说是两个受众群。电视剧、戏剧受众群的欣赏习惯,一般是最后希望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我的小说没有循着这个路子走,小说《装台》的刁大顺最后娶了大吊(剧中改名大雀)的妻子,这是对朋友生命托付的责任。女儿刁菊花外头折腾一圈后又回到生活原点(家里),仍然要让刁大顺望而生畏、操劳不尽。这种结局要放到电视剧里,估计很多观众不太能接受。按照影视创作规律将剧的调子变得更加温暖一些,体现了这门艺术对大众审美的适应。
从某种角度来说,文学和影视承担的功能既相同也不同,相同,都是引领社会的真善美;不同,可能文学的处理方式会更丰富、更多侧面一些,但这在影视呈现中也许会产生歧义,所以影视处理往往会更简洁、清晰一些。
记者:小说《装台》《主角》写作分别花了多长时间?一天写多少字,写作有没有碰到困难、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持续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创作并不容易,怎么坚持下来的?
陈彦:《装台》写了两年多,《主角》也写了两年多。写作都是用业余时间,周六、周日和节假日都在写。写《主角》时在陕西行政学院上班,充分利用了四个寒暑假的时间。有时工作日下班回去也能写上1000来字。
我反复说过,我的写作特点就是写最熟悉的生活。这样写起来才不会艰涩。拥有大的生活储备,才能做“压缩饼干”;反之,生活积累很少,就泡成了“胖大海”,效果不会好。从青少年时期起,自己就爱好文学,因为爱好,就能忍受住寂寞和痛苦,几十年,几乎把业余时间都交给它了。读读写写,写写读读,加上上班,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常和文学日常。写《主角》最早是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原名叫《花旦》,写了五六万字就放下了,原因是所写的东西太熟悉,什么都“往里钻”,写了一堆“婆烦生活”。调离后,跳出去再从“庐山”之外看,才捋得清晰一些,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看完《装台》,给了很多肯定和鼓励,说你何不再写一个“角儿”?我就把《花旦》翻出来,用两年多时间写成了《主角》。
记者:陕西文艺现象惹人注目,陕西作家群在全国影响很大,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声名赫赫。为什么陕西这片土地能产生这么多作家?现在您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能否谈谈地域文化对您的影响?
陈彦:每一地域都有它的文脉传承,独特的山川风貌、人情物理,必然形塑出不同的生命性情、天地人文。汉代的司马迁对陕西后来的文人影响很大。包括“关学”代表人物张载的“载道”精神,都是这块土地的精神生命重器。现代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无形中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影响。柳青到长安农村一待14年,下的功夫和其敬业精神对陕西作家影响很大。柳青有一句话叫“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写长篇小说耗体力,需要意志力。一部几十万字体量的长篇小说,总需修改四五遍吧。现在有电脑,修改相对容易了,而过去手写就非常艰难。《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是曹雪芹用毛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陕西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叫方英文,也是我的镇安老乡,他到现在还保持着用毛笔写长篇的习惯,这在全国大概独一无二,他既是作家,把自己也写成书法家了。
陕西“长安画派”涌现出了一批大画家,他们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这句话对各类创作都有启示。
“伸向传统”——陕西传统文化深厚,中华文明传统更深厚;“伸向传统”包含整个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不能局限在一城一池、一地一域。
“伸向生活”——我经常讲“两个阅读”:读生活,读书本。每个人接触的生活有限,在有限的土地上去接触生活,再通过阅读,了解别人的生活,了解整个世界,然后回过头来思考我们的人生,很多东西就开阔起来了。生活需要细咂细品、细嚼慢咽;阅读则需开疆拓土、波澜壮阔、冲出云层。
我大概有十几年在早晨一边跑步,一边背诵。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背过了,《四书》加起来也就五六万字,加上《庄子》的《逍遥游》《秋水篇》等,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和一些佛教经文,十几年也就背了十几万字,算下来一月也就1000多字。当然前边背过,后边也忘记了,大脑毕竟不是电脑储存,可也算是比较扎实地把儒释道的文化精髓“咀嚼”了一遍。读传统,读历史,读老剧本,读明清笔记,也读“先锋小说”,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读不懂,就硬读,找评论导赏来“按图索骥”。这部小说的名字尤利西斯就起自《奥德赛》里的主角名字,诗人荷马是在讲尤利西斯的10年英雄回归之路,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讲了一个软弱却充满了生命智慧的小人物一天的故事,反复读,就能从中悟出作者天马行空、纵横捭阖的思维、思考魅力。
现代性是和传统对照出来不是孤立形成的。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现代。有些现代是对传统的反叛,而更多的现代仍然是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社会肯定要向现代化进发,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现代和传统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撕裂,而是水乳交融、轩轾难分的,是驮着历史辎重前进的演进关系。
我近几年大量关注天文学,也是为了写作,在了解宇宙的时候,想到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外的古人,都是把眼睛向着天空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今天的深空探测,对创作者来讲,可能都是有大用的。尽管我不会去写科幻小说,但会因此改变一些思维方式,努力去寻找一种大的眼光和境界。从哈勃望远镜上拍到的地球,小得简直不值得人类去发动什么战争,更遑论个体仇恨。
记者:《装台》中的刁顺子有满满“正能量”,而《主角》中的忆秦娥似乎有点老庄哲学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处理呢?
陈彦:我这几十年就跟角儿打交道,他们的生活习性、人生欢乐与悲苦,他们生命的至暗与高光时刻,都比较熟悉。演员想成为“大角儿”,真正在一个剧种的一个历史阶段,形成一座高峰,我觉得只凭着脑瓜灵光是很难的。有些艺术就需要下“蠢笨”的功夫,才可能一点点建构起向天的塔尖。这无形中和老庄哲学有一种吻合,《庄子·达生》中驼背老人捕蝉之道就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太想成才,就必然急功近利,可能会走邪门歪道,反倒成不了才。即使成了才,也不会是大才,多数是热闹的匆匆过客而已。忆秦娥看似蠢笨,开始唱戏是去混饭吃,并不自觉;后来是“蒸馍不为吃,就图蒸(争)口气”;再后来才进入到“用志不分”的状态。要相信社会的力量,多数时候会正向出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当你锅里水太少,准备不充分,烧开也没多大沸点时,也就少有人给你拾柴添火。角儿的玉成,是天时地利和社会方方面面力道的结果,只有把握住了这个哲学辩证关系,才可能出现被一股脑儿推上山顶的时刻。
《主角》是我亲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对社会演进过程的一种思考:人到底应该怎么活着?怎么活着才自在?怎么活着又不自在?谁在推动我们活着?我们生命的制动系统又是谁等等问题。仅仅从励志角度看,写忆秦娥就没有什么认识价值和意义。这本小说我努力想展示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角儿的命运,是一群人的命运,也是一个时代的命运。
记者:《装台》和《主角》的人物要么和戏曲有关,要么是戏曲人,写作这种非大众化的专业群体却获得成功,原因是什么?
陈彦: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写一个叫亚哈的船长,带着一帮人在海上拼死拼活地捕捞一条叫莫比迪克的鲸鱼,从大西洋撵到印度洋、太平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写了并非广众职业的捕鱼生活,但都是深切人性肯綮的绝世佳作,将人们带入到了人性的马里亚纳深海沟。小说创作重要的不在于写哪一个职业、哪一种小的生活视域,而在于里面所涵养的人性深度,是不是对更多人有一种代入感。拼命去写最大众的职场未必能写出很优秀的作品。我觉得职业与人性有关系,但没有太过必然的联系。
记者:现在您的文学作品家喻户晓。实际上,戏剧是您的本行,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长达20多年,您编剧的戏剧作品屡获国家级大奖。“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是您的戏剧代表作,全部是现代戏,是有意为之?您有哪些创作技巧呢?
陈彦:我是一个游走于戏剧与小说之间的创作者,秦腔对我的影响很大。600多年有据可考的秦腔史,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丰富剧目,秦腔是我的一部百科全书。我也喜欢传统戏,目前我们对传统经典的改编做得还不够,我在里面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才开始写作现实题材作品。至于为什么老写现实题材,我觉得一个作家总有他表现的侧重面和手法,当下现实生活更能引起我的创作兴趣。
文艺作品要写热腾腾的生活,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生活气息里面透射出各种思想、价值观,如果我们直奔价值、思想去写,作品就没办法看了。创作要获得对生活的概括力,今天的作家面临的其实就是对社会生活概括力的问题。我们民族有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没有英雄模范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是匍匐在地、“一地鸡毛”的民族。但是应该怎样塑造英雄,真正让他们鲜活地流动在民族的血脉里、存活于我们的心中,就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很多英模人物事迹非常感人,可创作出来后,形象就虚假、二维扁平化了,这意味着我们的概括能力、认知能力、洞穿能力、塑造能力都还不够,要真正走向世界,得有我们无尽的被人认同的民族精英和平民英雄的故事。但的确要认识到塑造这种人物的难度,比如《大树西迁》的写作,就是写上世纪50年代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故事。我在上海交大博士楼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住了4个多月,采访100多人,把交大历史也是反复研读、揣摩,本来是要写几十集电视剧的,最后却只写出了两万多字的舞台剧,连我当时做的笔记的1/10都不到。它的创作就是思考各种概括的可能性,怎么把这种西迁精神用一种高度的、凝练的方式概括出来。最终没有写体量庞大的电视剧,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够概括它的故事。
我始终认为创作技巧是第二位的,不难学到,包括编剧技巧,唯有内容永远气象混沌、难以捉摸,也永远劳人而又揪心。把范本看一两遍,就能模仿,但模仿的只是外壳,重要的是看这些技巧是否适合要塑造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好的手法能采用时就采用,不能采用的时候不要硬采用。就像演员表演的风格化是好事情,但一味强调风格的时候,这个演员的表演就非常虚假了。有些人常常为了追求一种风格,将自己固化在很小的范围内,把一种其实是套路的东西放得很大,自然就把丰富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都挤压过滤掉了。
记者:您的作品常常观照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打动人心。
陈彦:我自己也是从底层出来的。当我从小接触的这群人来到大城市生活时,自然会引发我的关注。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宝塔尖顶的,大厦的基石是靠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支撑着。文学艺术画廊中应该有他们不屈不挠的群像。他们的生活、精神、情感值得一个文明的社会去关注和洞悉。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生命亮色被遮蔽太多了,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深入开掘他们的生命价值与光亮。
《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父亲腰摔断了,母亲又出车祸去世,为照顾家里几个弟妹,她做出了艰难抉择,放弃了上大学。人生的这次变轨,让她成了社区一个最普通的女性,而几个弟妹都从大学毕业,高过她人生一大截。这种人在社会中大量存在,如果没有他们肩膀的支撑,很多家庭都会柱倒梁塌甚至分崩离析。我认为当时这个作品的核心要义在于思考了社会是否还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整个社会的基础建设,都是很多普通劳动者创造的,我想不能仅仅把他们定位在“打工挣钱”的价值上。这需要做社会学思考。有些人接受不了《装台》里塑造的刁菊花这个人。现在,这样的孩子大量存在着,他们希望有体面的父母,希望一出生父母就给他们好的物质基础,渴望香车豪宅、名牌包包。如果父母不能给予,还在肩扛背驮讨生活,他们的内心就发生扭曲,把愤恨的锅,无情地扣到“无能”的父母身上。刁菊花的人物形象,是对社会的一种警示,也是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当然电视剧把她改温暖了,这很好,转变也是一种醒世。
我们要给社会最普通的劳动者以基本的尊重和尊严,并应开凿出他们的生命价值光亮。关注小人物,是一个世界性的文艺创作话题。
记者:生死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您的作品给人感觉是温情的、有希望的。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陈彦:如果世界没有希望,人类还怎么活下去,文学艺术必须给人以希望,尤其是要给普通人以温情、温暖与希望。我们得给人生煨起一堆向天的火焰,这是我以为的写作意义。当然,我的每个作品也都涉及悲苦甚至死亡。小说说到底是在唠叨生活,凡生活里出现的,还有我们想象力能够着的,都得唠叨唠叨。说到下一步创作,长篇小说《喜剧》马上就要出版,写了在舞台上演小丑的父子三个人,以及由他们散枝开叶所带出来的百十号人的演艺、生存故事,当然,也是在借他们的灵魂,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还是不惹人发笑的为好。最早写《喜剧》的时候是十几年前,当时叫《小丑》,跟《花旦》一样没有写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时间充裕,就把它写完也改完了。由于有个电影叫《小丑》,很有名,我不敢掠其美,就改名《喜剧》了,因为是在说一群喜剧演员的生活。它与《装台》《主角》一样,有戏里,也有戏外。有小舞台,也有广阔的社会人生。
记者:这些年您的工作单位、职务几经变化,却始终坚持创作。从戏曲院团的带头人,到行政机关做管理,然后又到了北京主持中国剧协工作。您如何看待这种职务、身份上的变化?作为中国剧协驻会负责人,在推动戏剧发展上有哪些想法?
陈彦:我有一个主张,作家尽量不要太过专业化,尤其是在中青年阶段,这可能会固化自己的圈子和认知。西方很多作家是媒体记者出身,接触生活广泛,采访就是认识生活、接触各种对象的过程。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各种窗户都打开,就可能得到更多信息。视野开阔对写作尤其是思维的经纬度是有利的。现在回头看,如果我没有参与到具体的公职生涯里去,那今天也就不会有《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我的写作也会缺少很多维度与参照系。所以,紧紧抓住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的那些特别场域的丰富体悟,是十分重要的。我写舞台人的人生,不是体验生活,那就是我的实际生活。在那里没写出来,到其他单位写出来了,这叫走出“庐山”看“庐山”。
一个人的工作能与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是最好的。到中国剧协工作,与自己的专业结合得很好,视野更加开阔,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同时也能把自己对于戏剧以及创作的思考和更多同行进行分享,是很好的调整和转型。
戏剧已是阅尽千年历史的成熟老人,无论是中国戏曲,还是从西方借鉴来的话剧,历史都很长,都有非常成熟的创作规律,要严格按照创作规律去为当下和历史留下其独特的痕迹。创新,是攀上前贤肩头后的纵身一跃,而不是摒弃先贤生命艺术结晶的“扮鬼脸”和“怪叫声”。戏剧老人见多识广,经验丰赡,“老生”随便张口一谈,都是警句和金玉良言,令人敬畏不已。简单总结起来,仍是“出人、出戏、多演出”这7个字,三者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缺一而必寿终。艺术创作要精心营构,越是想弄出“大动静”,越需要下狠功夫甚至是很蠢笨的功夫,而半点都不敢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最重要的,还是要推出让老百姓拥到台前看了舍不得走的好戏、好角儿,并且能口碑炸裂、传之久远、历久弥新。我想那就是人民性,那就是价值观,那就是最终的审美评判。